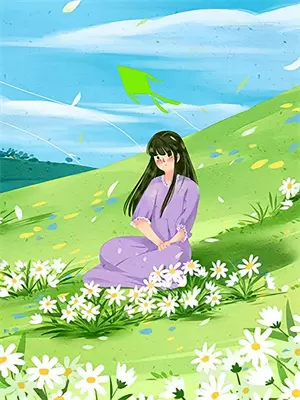- 机修班的风声(陈志远沈玉梅)最新小说全文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机修班的风声(陈志远沈玉梅)
- 分类: 其它小说
- 作者:一一悸动
- 更新:2025-09-28 19:38:19
《机修班的风声(陈志远沈玉梅)最新小说全文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机修班的风声(陈志远沈玉梅)》精彩片段
一九七五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迟,已经是三月天了,
清河机械厂围墙边的迎春花才零零星星冒出几点黄。
厂区高音喇叭正放着《大/海/航行/靠/舵/手》,车间里的机床轰隆隆运转,
机油和金属的气味混杂在潮湿的空气里。沈玉梅站在铣床前,额角沁出细密的汗珠。
她今年二十八岁,在机械厂已经工作了十年。鹅蛋脸上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,
只是那眼里总藏着几分谨慎。乌黑的辫子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,蓝色工装虽然洗得发白,
却熨烫得平整挺括。“玉梅,零件加工好了吗?”车间主任王大柱走过来,声音洪亮。
“快了,王主任,还有最后一道工序。”沈玉梅轻声回答,手上的动作更加利落。
她知道自己在这厂里的处境——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,就像没有树荫的苗,
稍微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来过多关注。五年前,她那在煤矿工作的丈夫在一次事故中去世,
留给她的只有一间不足十五平米的平房和一个才三岁的儿子。从那时起,
沈玉梅学会了用低调和能干来保护自己。她加工的零件合格率总是车间第一,
却从不争抢先进名额;她容貌出众,却总是低着头走路;她独自抚养孩子,
却很少在人前诉苦。下班铃声响起,工人们潮水般涌向厂门。沈玉梅仔细清理完机床,
最后一个离开车间。“玉梅,等等!”厂办的女干事赵玉梅追上来,
神秘地压低声音:“听说上面要派工作组来咱厂搞技术革新,
厂里要抽调各车间的技术骨干成立攻关小组呢。”沈玉梅只是笑笑,没有接话。
这些消息离她太远,她关心的只是这个月能多拿几个加班费,给儿子小强买双新球鞋。
然而几天后,
厂部的一纸通知打破了沈玉梅平静的生活——她真的被选入了厂里的技术攻关小组。
周一早晨,当沈玉梅走进从未踏足过的厂部会议室时,七八个男工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看她。
在清一色深蓝工装的人群中,她注意到一个陌生面孔——一个三十出头、戴眼镜的男人,
穿着半旧的中山装,正低头看着图纸,眉头微蹙。
“这位是省机械局派来指导我们工作的陈工程师,陈志远同志。”厂长介绍道。
陈志远抬起头,与沈玉梅的目光相遇。他点点头,表情严肃,随即又低下头去。会议开始后,
陈志远的发言让在场的老工人都暗自吃惊。他不仅对厂里各种设备的型号、性能了如指掌,
还能准确指出生产工艺上的问题。沈玉梅坐在角落,
悄悄观察这个说话不紧不慢却逻辑清晰的男人。“铣床组的沈玉梅同志来了吗?
”陈志远突然问道。沈玉梅愣了一下,轻声应答:“来了。
”“图纸上这个零件的加工精度要求很高,听说你是全厂最擅长精细加工的铣工,
有什么想法吗?”陈志远推了推眼镜,目光透过镜片直直看向她。会议结束后,
沈玉梅正准备离开,陈志远叫住了她。“沈同志,能带我去车间看看实际加工过程吗?
”车间里,沈玉梅熟练地操作着铣床,陈志远站在一旁静静观察。
当沈玉梅提出一个改进夹具的小建议时,陈志远眼中闪过惊喜。“你很懂机械原理。”他说。
“我父亲原来是机械厂的八级工,小时候常教我看图纸。”沈玉梅轻声解释,
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对外人提起父亲。就这样,在接下来的一周里,
沈玉梅和陈志远因为工作接触越来越多。陈志远惊讶地发现,
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工对机械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力;而沈玉梅也感到陈志远与其他干部不同,
他尊重工人意见,从不摆架子。然而,厂里开始有了风言风语。“怪不得能被选进攻关小组,
原来是有两下子。”食堂里,几个女工窃窃私语,声音刚好能让邻桌的沈玉梅听到。
沈玉梅低头快速吃完饭,起身离开。这样的议论她不是第一次听到,
但这次心里却莫名地难受。周五下班时,天空飘起了细雨。沈玉梅忘记带伞,
只好用布包遮住头,小跑着向厂门走去。突然,一把黑色雨伞撑在了她头顶。
“我送你到厂门口。”陈志远不知何时出现在她身边。两人沉默地走了一段,
陈志远突然开口:“厂里的闲话,你别往心里去。”沈玉梅一愣,
随即明白他也听到了那些议论。“我习惯了。”她淡淡地说。“这不公平。
”陈志远的声音有些激动,“你是我见过最懂技术的工人,那些议论是对你能力的不尊重。
”沈玉梅停下脚步,第一次认真地看着这个戴着眼镜、一脸书卷气的男人。多年来,
她听到的要么是同情,要么是轻浮的调侃,却很少有人这样直接地肯定她的价值。“谢谢。
”她轻声说,眼角有些湿润。分别时,
陈志远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书:“这是《机械设计基础》,我想你会感兴趣。
”沈玉梅接过书,指尖不经意间触到陈志远的手,两人都微微一颤。那天晚上,
沈玉梅在灯下翻看着陈志远给的书,书页间偶尔有铅笔写的批注,字迹工整有力。
她发现自己竟然想象着陈志远在灯下看书的样子。攻关小组的工作持续了一个月。
在这段时间里,沈玉梅和陈志远合作解决了厂里多年的技术难题。随着接触增多,
他们之间的默契也越来越深。有时一个眼神,就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。然而,
沈玉梅也察觉到周围异样的目光越来越密集。车间主任找她谈话,
委婉地提醒“要注意影响”;好友赵玉梅悄悄告诉她,
有人已经向厂领导反映了“作风问题”。最让沈玉梅担心的是,
她发现自己开始期待每天与陈志远见面的时刻。这种期待让她既甜蜜又恐惧。
项目结束的前一天,陈志远约沈玉梅到厂区后的小树林见面。暮色四合,
远处车间的灯光零星亮起。“我下周就要回省城了。”陈志远说。沈玉梅的心沉了一下,
但她只是点点头:“哦。”“玉梅,”陈志远第一次直呼她的名字,
“有句话我一直想说...我欣赏你,不只是因为你的技术。”沈玉梅抬起头,
在渐浓的暮色中看着陈志远认真的脸。“我知道你的情况,我不在乎那些。
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。”陈志远继续说,“我回去后可以申请调来清河机械厂,
如果你也愿意...”“别说了!”沈玉梅突然打断他,“这不可能的。”“为什么?
因为你是寡妇?因为我比你大几岁?还是因为别人的闲话?”陈志远的声音有些激动。
沈玉梅摇摇头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:“你会后悔的。这样的关系,在这样的地方,
你会被拖累的。”“我不怕!”陈志远抓住她的手,“玉梅,新时代就要来了,我看得出来,
国家就要变了,人们的思想也会变的。”沈玉梅抽回手,转身跑开了。那一夜,她失眠了。
陈志远离开后的日子恢复了平静,但沈玉梅的心却再也回不到从前。
她发现自己总会不自觉地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,听到厂里有省城来的消息就会格外留意。
一个月后,赵玉梅神秘兮兮地找到她:“玉梅,你听说没有?陈工程师又回来了,
说是长期派驻我们厂指导工作呢!”沈玉梅的心猛地一跳。这时,
车间门外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陈志远站在那里,微笑着看着她。“沈玉梅同志,
我又来麻烦你了,新项目需要你的帮助。”他大声说,语气公事公办,
但眼神里藏着只有她才懂的温度。下班后,在无人的车间角落,
陈志远悄悄塞给沈玉梅一封信:“看完再答复我。”信很短,只有一行字:“时代会变,
我的心不会变。你愿意等我吗?”沈玉梅抬起头,看着面前这个固执的男人,
突然觉得那些压得她喘不过气的流言蜚语都不重要了。她轻轻点了点头。远处,
高音喇叭正在播放新闻,隐约能听到“四个现代化”的字眼。春风吹过机械厂大院,
墙角的迎春花不知何时已经开成了一片灿烂的金黄。沈玉梅那轻轻的一点头,
仿佛用尽了她积攒五年的勇气。点头之后,是长久的沉默,两人站在逐渐暗下来的车间里,
只能听到彼此有些急促的呼吸声。最终还是陈志远先开了口,
声音比平时低沉:“那就说定了。外面……外面天黑了,我送你到厂门口。”这回,
沈玉梅没有拒绝。回去的路上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,陈志远撑开那把熟悉的黑伞,
小心地保持着既不疏远也不冒犯的距离。伞下的空间有限,
沈玉梅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肥皂味和墨水味,一种属于知识分子的干净气息,
与她日常接触的机油和金属味截然不同。“厂里可能会有些难听的话,”快到厂门口时,
陈志远停下脚步,看着她说,“你别一个人扛着,有我呢。”沈玉梅抬起头,
雨水在伞面上敲打出细密的节奏,厂门口昏黄的路灯勾勒出他认真的侧脸。她心里五味杂陈,
既暖又酸,最终只是轻声说:“我知道怎么做。你……你也小心些,人言可畏。
”陈志远这次是作为省机械局长期派驻的技术顾问回来的,厂里给他分了一间小小的宿舍。
他的回归,以及他明显与沈玉梅增多的接触,果然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,
在清河机械厂激起了层层涟漪。
车间里的风言风语渐渐从窃窃私语变成了半公开的调侃和指责。“瞧见没,又去找那位了,
说是讨论技术,谁信啊?”铣床组一个惯爱嚼舌根的女工斜眼看着沈玉梅走向技术科的背影。
“人家是寡妇门前是非多,陈工可是未婚的青年才俊,别是让人迷了心窍……”有人附和道。
车间主任王大柱也找沈玉梅谈过一次话,语重心长:“玉梅啊,你是厂里的先进,
要注意影响。陈工是上面来的专家,你们……走得近,难免有人说闲话。你是女同志,
名声要紧。”沈玉梅垂着眼睑,手指紧紧攥着工装衣角,心里涌起一股屈辱和愤怒。
但她知道,辩白只会越描越黑,只是平静地回答:“王主任,
我和陈工讨论的都是工作上的技术问题,是为了解决铣床三组的加工精度难题,有记录可查。
清者自清。”然而,压力不仅来自外界。一天傍晚,沈玉梅去托儿所接儿子小强。
六岁的小强仰着脸问她:“妈妈,他们说你要给我找个新爸爸,是那个戴眼镜的陈叔叔吗?
”沈玉梅的心猛地一揪,蹲下身看着儿子稚嫩而困惑的眼睛:“小强,你喜欢陈叔叔吗?
”小强想了想,用力点点头:“陈叔叔给我用木头做过小卡车,还教我认图纸上的零件,
他说我长大也能当工程师!”儿子的话像一股暖流,瞬间冲散了沈玉梅心头的阴霾。
同类推荐
 我把冰淇淋月饼换成五仁送给婆婆,她竟吃出大金条(千张包陈嘉明)完结版小说_最新全本小说我把冰淇淋月饼换成五仁送给婆婆,她竟吃出大金条千张包陈嘉明
我把冰淇淋月饼换成五仁送给婆婆,她竟吃出大金条(千张包陈嘉明)完结版小说_最新全本小说我把冰淇淋月饼换成五仁送给婆婆,她竟吃出大金条千张包陈嘉明
千张包
 回忆嵌在残月中(顾怀瑾林晚棠)完结版免费阅读_回忆嵌在残月中全文免费阅读
回忆嵌在残月中(顾怀瑾林晚棠)完结版免费阅读_回忆嵌在残月中全文免费阅读
米瑞
 订婚宴上,婆婆怒骂我送的帝王绿翡翠是玻璃(张春芳刁玉亮)最新完结小说推荐_热门小说排行榜订婚宴上,婆婆怒骂我送的帝王绿翡翠是玻璃张春芳刁玉亮
订婚宴上,婆婆怒骂我送的帝王绿翡翠是玻璃(张春芳刁玉亮)最新完结小说推荐_热门小说排行榜订婚宴上,婆婆怒骂我送的帝王绿翡翠是玻璃张春芳刁玉亮
六六吖
 民宿林明珠(国庆节和妈妈一起被赶出爸爸开的民宿,跆拳道黑段的我生气了)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民宿林明珠全集在线阅读
民宿林明珠(国庆节和妈妈一起被赶出爸爸开的民宿,跆拳道黑段的我生气了)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民宿林明珠全集在线阅读
微微飘尘
 爱雌竞的妈妈想抢走我老公(佚名佚名)完结版免费阅读_爱雌竞的妈妈想抢走我老公全文免费阅读
爱雌竞的妈妈想抢走我老公(佚名佚名)完结版免费阅读_爱雌竞的妈妈想抢走我老公全文免费阅读
知我意
 实习生利用塔罗牌占卜造谣后,我杀疯了叶晴付圆圆小说推荐完本_热门小说大全实习生利用塔罗牌占卜造谣后,我杀疯了(叶晴付圆圆)
实习生利用塔罗牌占卜造谣后,我杀疯了叶晴付圆圆小说推荐完本_热门小说大全实习生利用塔罗牌占卜造谣后,我杀疯了(叶晴付圆圆)
三丰
 老公认保姆当老婆后,崩溃了(刘春燕宋修谨)完本小说_热门的小说老公认保姆当老婆后,崩溃了刘春燕宋修谨
老公认保姆当老婆后,崩溃了(刘春燕宋修谨)完本小说_热门的小说老公认保姆当老婆后,崩溃了刘春燕宋修谨
辞子
 从此再无朝与暮(贺沉屿宋意枝)小说最新章节_全文免费小说从此再无朝与暮贺沉屿宋意枝
从此再无朝与暮(贺沉屿宋意枝)小说最新章节_全文免费小说从此再无朝与暮贺沉屿宋意枝
炸鱼
 芒果外宾(被为我好的妈妈害死后)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(被为我好的妈妈害死后)完结版免费在线阅读
芒果外宾(被为我好的妈妈害死后)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(被为我好的妈妈害死后)完结版免费在线阅读
香菜蛋挞
 相思流年尽成灰(顾景辞莫知沅)完本小说大全_热门小说大全相思流年尽成灰顾景辞莫知沅
相思流年尽成灰(顾景辞莫知沅)完本小说大全_热门小说大全相思流年尽成灰顾景辞莫知沅
倾情一舞02